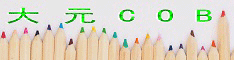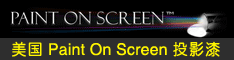近來到故宮參觀的朋友一定會發現,古老的皇家宮殿如今也已經與數字科技聯姻。如今只要一踏進故宮端門,就可在數字成像、定位系統、虛擬現實等技術的幫助下“一覽故宮曉”。故宮,正在用一種數字媒體技術與古典建筑融合的方式,用一種體驗式、沉浸式的交互手段來講述它的前世今生,使人們推開中國古典文化與歷史的大門變得更加輕松。
本期,我們就故宮“端門數字館”項目邀請到另一位嘉賓,是主持故宮端門數字館視覺形象設計、數字沙盤及《寫生珍禽圖》數字繪畫項目的交互體驗設計及內容制作的央美副教授、數碼媒體工作室的費俊老師。為大家揭曉這個堪稱世界首次將整體古典建筑完全用作數字化展示的項目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技術手段、以及未來科技與文博領域結合的趨勢。
記者:請費俊老師老師來介紹一下你們所參與的項目吧?
費俊:丹青把整個端門數字館項目的發展歷史給大家有了一個展現,讓大家有了宏觀的認識。我自己,包括某集體、央美團隊,也很榮幸參與到了這個項目。在過去的兩三年時間里,我們參與了不少故宮的文化項目,像端門這么大體量的項目,就像丹青說的,這里面有大量的團隊的合作和協作。更重要的是,故宮并不是大家看到的,突然做了一個端門數字館,其實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們已經在博物館的數字化方向上做了很多的積累。
另外,也就是說,基于這些豐富的數字資產的再開發,這其實是故宮的很多部門,尤其是故宮的執行部,有很多的專家和老師,他們對這些可以開發的數字資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進行選題、策劃。
那我們介入到端門項目也是兩年前,當時我們也試圖參與到整體項目的規劃中。但最終故宮采納了清華團隊的方案,但也很榮幸,大家都有各自的設計思路,我們覺得能跟清華團隊一起參與這個項目也是非常幸運的事情。在基于清華的整體空間、交互裝置的設計理念上,我們介入到了三個具體項目的交互體驗設計以及內容制作方面。下面我簡單介紹我們參與的三個項目:第一個項目是位于端門數字館中間的大型裝置作品,叫做數字沙盤。

大家從這個圖上可以看到,它其實是由四塊屏幕組成的,這個在丹青的方案中就有這樣的設定。看似它是有環繞劇場的體驗感,因為無論是地面屏幕,還是兩側的數字宮門屏幕和北側的數字屏,都有這種感覺。但其實我們在進入到內容的交互體驗設計中其實面臨著很大的挑戰,那么其中一個挑戰,當人們在觀看動態電影時候,人的關注點和聚焦點是不可以被過多地分散的。那么也就是如何處理好這四塊屏之間的內容節奏和同步以及與觀眾的互動可能,就成為這個課題里最重要的,我們叫做用戶體驗的問題。

大家現在看到的是基于現場裝置實拍的圖片。 經過一段時間和故宮執行部的專家一起來研究,如何基于這四塊屏來進行演示,最后我們確定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這個方案。這個方案的特點是,我們對四塊屏的敘述功能有了明確的界定,北面的屏,主要介紹了一個皇宮變成了博物院的歷史。地面這塊屏幕,它更多是承擔了一個動態沙盤的角色,也就是它主要的職能是客觀地動態展示故宮的格局以及故宮各個區域不同的功能。

而兩側的屏幕,就像這張圖,更多的是輔助北屏,輔助地面沙盤,呈現出一些烘托氣氛,以及進一步說明故宮收藏和場館內容。

后面這四張圖,基本上來自北屏的歷史性專題片的截圖,交代了故宮博物院是如何從歷史上逐步從紫禁城演化成博物院,重要的歷史時刻,以及宮殿本身在規模和形制上的變化。

這兩張黑底圖,其實是地面沙盤的狀態圖,大家可以看到故宮整個規劃的格局,包括不同宮殿之間的格局關系。還有一種重要的需求是,數字沙盤需要有導游和專業人員在后面講解的。所以我們還特別為沙盤研制了一個控制端,可以給演講者控制,如何按照自己的節奏給觀眾介紹故宮,通常用戶在現場不一定能看到這個控制端,這是現場演講人員提供的一個很重要的溝通工具。

第二個項目叫做《寫生珍禽圖》,它實際上是一個基于觸摸屏的項目,觀眾和它的交互方式是觀眾湊近大約1米多時,這個屏幕中的珍禽異獸就會開始騷動起來。當你靠近這幅數字繪畫作品時候,首先它會用一段動畫影片來簡單介紹這幅畫的由來。因為它是五代宮廷繪畫大師黃泉唯一一張可信的傳世作品,里面有24只栩栩如生的珍禽還有昆蟲,我們的目標是能不能把這幅畫背后的珍禽異獸的習性、自然知識也能為大家呈現出來。當觀眾點擊上面的某只鳥,就會展開這只鳥棲息的環境,你可以通過對畫本身的體驗式的欣賞,擴展了解到關于鳥本身的知識。
那么這樣一個選題,是由故宮執行部的多位老師來首先進行策劃,同時邀請到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專家,故宮書畫部的專家,對這些畫中的鳥、珍禽做非常學術化的鑒別,我們演繹的所有內容必須符合客觀自然。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項目,難點不是在于我們能不能夠惟妙惟肖地把事物畫出來,而是在于如何符合客觀條件,同時還能夠藝術化地表現。其實大家能看到,這上面幾乎有上萬張用手繪方式來復原的名畫,我們希望在動畫過程中,盡量不去損壞原畫本身的非常優美的繪畫質感。
當然另外在交互設計上的特點,我們希望最后的成品是無UI的形式,能夠簡化掉的按鈕,我們盡量簡化掉。

在這里大家看到的這些設計過程的圖,其實為了說明一個問題,所有之前的UI設計最后都被我們自己給消滅掉了,我們經過了一個痛苦的復雜的過程,最后決定形成這樣一種無UI的形式。所以我們說做減法是很困難的,但是希望能夠做出一個非常極致的體驗作品,那減法又是必經之路。
那之所以要追求這樣一種無UI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充分體現出我們對于原畫的一種尊重,因為在這樣一幅大師的作品面前,就是做的再美的UI,也無法與原畫匹配。

最后簡單講幾句關于故宮VI形象,其實用比較簡潔的幾何形方式來概括這個形象其實非常有難度。我們除了做LOGO的設計,還要考慮它在故宮項目上的應用。
最后我還想提,其實這么一個龐大的項目,都是由多方努力建成的。首先是故宮博物院,包括具體到故宮執行部門的眾多老師和專家,他們從策劃選題到最終指導執行,同時還有大量參與很多交互設計的團隊。

記者:您覺得目前對于博物館數字化的過程中,最為困難的部分是在于技術還是在于文化呢?
費俊:針對這個問題我想說,其實在博物館數字化的過程中,最困難的不是在于技術,而是在于文化轉義本身。我說的文化轉義是指如何能夠用更有效的從設計到技術的方法,把收藏有效地轉義出來,形成我們所看到的無論是app還是交互裝置。面對這樣一個基于經典作品的文化內容,如何打開原畫的一個多維度的內容,進行內容的現代演繹,如何利用交互設計基于當下語境的傳達和體驗?我們最大的心得和挑戰是:尊重原畫。文化轉譯無法只通過視覺設計實現,必須基于文化內容做好規劃。文化轉譯是設計的核心工作。
記者:文博與數字科技相結合在近幾年越來越流行,幾乎在一些大型的博物館如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國家大劇院等一些條件的公共文博單位都能見到。文博領域搭載現代的數字科技,這種變革,對傳承和傳播中國文化和藝術意味著什么? 未來發展趨勢會怎樣?
費俊:在我看來,數字科技和文化遺產包括和博物館的結合,可以帶來三個比較大的意義。首先第一個是保護的意義,第二個是傳播的意義,第三個是傳承的意義。我們大量的文物在歷史迭代過程中毀壞。那么更可怕的還不是這種毀壞,而是現代人與祖先的文化積累上的斷代。所以我們說談到保護的意義,大家很容易理解。像故宮博物院這種最繁忙的博物館,一直都在超載超負荷地承載參觀者。那即使故宮已經非常慷慨打開大門迎接參觀者,其實還有大量的中國人和外國游客還沒有條件進入故宮去進行體驗。所以我們說數字技術其實是非常低成本的,幾乎是零復制成本的,把文化作為一種可體驗的,可以觸碰的,可以交互的產品,以極強的傳播力,把它發行到世界各地。當然我們不是簡單地把一個數字內容放到互聯網傳播,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構建一種和當下年輕人能夠理解的語言相關聯的方式,使它成為不僅是可以被傳播的,也可以與年輕人互動的,被體驗的,被消費的形態。就像我們也在嘗試做一個項目叫做“城市博物館”,我們有沒有可能基于我們所生活的都市,像北京這樣有豐富歷史文脈的地區,用數字手段在這個城市上疊加城市的歷史、故事、包括遺失的廟宇、拆掉的城墻,用虛擬博物館的概念實現。我相信在中國這樣一個文物缺失的地區,數字科技就顯得尤為重要,某種意義上它成為一種文化修復工具。
記者:那么請費老師也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吧,如果作為一名交互藝術方向的學生,應該如何規劃自己的職業方向?參與什么樣的項目?
費俊:交互藝術與設計是一個非常跨學科的專業,它和傳統劃分的平面設計、工業設計、展覽設計、建筑設計等學科都有交集,在互聯網、智慧城市、智慧博物館、智能硬件、智能交通等領域中都有極其廣闊的應用前景。作為交互設計的學生,我認為需要掌握三個核心能力:1、交互設計基本技能,2、用戶為中心的設計方法, 3、跨專業設計能力。第一個能力指的更多是基于從UE到UI的設計基礎,包括基于屏幕的界面設計,也包括基于物理互動的設計基礎。第二個能力是了解用戶需求的能力,它能幫助設計師從產品設計層面來把握。第三個能力其實是融會貫通的能力,它要求設計師能夠更加廣義的理解“界面”和“交互”,用整體設計的理念來駕馭跨專業和跨行業的項目。至于職業規劃,有了上面的三個能力,應該不再是去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你。